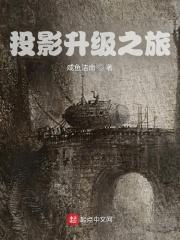九一文学>臣心匪石 > 潜龙游14(第3页)
潜龙游14(第3页)
“怎么了?”秦渊澈在他对面坐下,语气温和而关切。
“中了贡士,这是天大的喜事,往后便是进士老爷了。”
“怎的看你……似乎心事更重了?”他顿了顿,试图理解。
“可是在担忧殿试?以你的才学,定然无碍的。”
秦卿许抬起头,看着兄长被烛光映照的、写满关切的脸庞,心中涌起一股暖流,旋即却被更深的孤独所淹没。
有些心事,如山如海,却无法对最亲的人诉说分毫。
他勉强牵动嘴角,露出一丝疲惫的笑意,低声道:“没什么,大哥。”
“只是觉得……像做了一场光怪陆离的梦,一时有些恍惚。”
秦渊澈只当他是连日紧张,突逢大喜,心神激荡所致,便笑着宽慰道:“傻话!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功名,锣鼓鞭炮、官报捷文都是真的。”
“咱们秦家以后就真是诗书传家了,你如今是贡士老爷,往后殿试面圣更要谨言慎行,沉稳持重,方不负这身功名。”
他说着,语气中不自觉地带上了商贾的盘算,“如今你有了这功名,便是有了官身,以往那些总嫌咱们家是商户不肯深交的清流人家,往后也得递帖子登门,这对家里……”
听着兄长絮絮叨叨说着家族声望、人际往来以及未来的官场经营,秦卿许心中那点空洞感愈发扩大,仿佛自己与这热闹喜庆的世界隔着一层透明的壁垒。
他理解兄长的喜悦与期望,那是世俗中最正常、最合理的反应。
可他的灵魂仿佛被撕裂成了两半,一半在努力扮演着新科举人、光耀门楣的角色,另一半却独自沉溺在无人可诉、冰冷彻骨的深渊里。
“……明日里,怕是有同科的邀约,鹿鸣宴也是要去的,还需拜会座师房师……”秦渊澈还在兴致勃勃地规划着。
“大哥。”秦卿许轻声打断他,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,声音飘忽。
“宫中……斋宫那边,可有什么新的消息?”
秦渊澈的话音戛然而止。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起来,沉默了片刻,轻轻叹了口气:“听说……陛下仍在静养,未曾出斋宫半步。春祭大典前的诸多仪程,听闻都是由礼亲王代行的。”
他仔细观察着弟弟的脸色,小心地补充道,“你也别太挂心了,陛下是真龙天子,自有百灵护佑,定会龙体康健,如期主持大典的。”
“你如今已是贡士,很快便要面圣,更需稳住心神,万不可在御前失了仪态。”
仍在静养。
仪典仍需代行。
秦卿许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缓缓攥紧,一点点沉入冰冷的湖底。
白日里所有的喧嚣、恭维、荣耀,在这一刻都褪尽了颜色,变得轻飘无力。
贡士功名,锦衣华服,却无法穿透那重重宫墙,换得那人一丝真正的安康。
这即将到手的荣华,于他而言,究竟意义何在。
他端起那盅尚且温热的燕窝,机械地舀了一勺送入口中,清甜润滑却品不出半分滋味,只余满口涩然。
“我明白。”他低声应道,声音平静无波,听不出任何情绪。
秦渊澈看着他,张了张嘴,似乎还想说些什么,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轻叹,伸手用力按了按他的肩膀:“万事有大哥在,你……早些歇息吧,明日开始,且有的忙呢。”
兄长离开后书房重归彻底的寂静。
秦卿许独自坐在灯下,目光再次落在那份捷报和那袭青衣之上。
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,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和崭新的起点,却华美而冰冷,像一个精致而沉重的枷锁,正式将他纳入那套他既渴望靠近又本能恐惧的、庞大而复杂的权力机器之中。
贡士郎。
秦卿许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崭新的身份,感受到的不是平步青云的喜悦,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令人窒息的责任和无边无际的孤独。
这条用无数心血,难以言说的情感与惊惧铺就的仕途,终于在他面前展开了第一步。
而这条路的尽头,是能得见天光,窥得一丝妄念实现的可能,还是通往更深的迷障与无法回头的绝境,他无从知晓。
他唯一知道的是从今往后他的每一步一步都将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
不仅仅是为官之道,更是为心之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