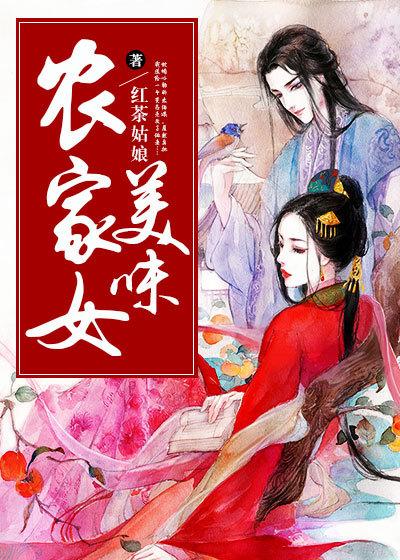九一文学>误认攻略的九周目,我想折断死亡Flag! > 第 23 章 暖光与荆棘的午后(第1页)
第 23 章 暖光与荆棘的午后(第1页)
“从青森那样遥远的地方独自前来,一定……很辛苦吧。”
铃木裕也的声音像午后晒暖的溪水,平稳而带着回忆特有的温润光泽。
他的目光掠过公园里抽芽的树枝,变得有些悠远。
“气候、饮食、人们的说话节奏甚至街道的气息……全都变了样,像是被突然抛进了另一个世界的缝隙里。”
“我当年从小地方来东京读大学时,也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年,才觉得脚尖终于触到了地面。那时葵还在上高中,每次我周末打电话回家,她接起电话的声音总是裹着一层薄薄的水汽,说想家,说东京好大好吵,说便利店的热柜永远不像妈妈刚蒸好的包子……我就拼命打工,攒出新干线的票钱,哪怕只能回去待一天。”
“带她去吃她念叨了很久的草莓芭菲,陪她在黄昏的书店挑参考书,听她絮絮叨叨讲那些在我看来细小如尘、在她世界里却重如山峦的事——同桌换了新发卡,数学测验错了一道不该错的题,邻班那个总在篮球场挥汗的男孩今天看了她一眼……”
他讲述的语调平和真挚,那些关于成长、分离与笨拙牵挂的碎片,在春日午后的光里缓缓铺展。
雾岛莲安静地听着,偶尔轻轻地点头,视线落在喷泉池荡漾的粼粼碎光上,仿佛能从那些破碎的明亮里,窥见另一个遥不可及次元的倒影。
这些事,于她而言,遥远得像隔着毛玻璃听来的、别人的童话。
她没有兄弟姐妹。
在那些被血色与绝望浸透的轮回里,“亲情”这个词,往往与“软肋”“弱点”“可利用的筹码”冰冷地画上等号。
像这样不掺杂任何算计、不包裹任何表演的纯粹羁绊,陌生得让她指尖微微发麻。
铃木葵对她毫无缘由的亲近,此刻铃木裕也自然流淌的善意,都让她感到一种……细微的、近乎无措的困惑,以及一丝她不愿深究的、类似锈铁摩擦心脏内壁的刺痛感。
为什么?
她明明在利用他们。
利用铃木葵的单纯,加固“雾岛莲”拥有“普通社会联结”的证明。
利用这次会面,制造“正常社交活动”的行为记录,以备日后更严苛的身份核验。
可这对兄妹,却用近乎透明的真诚,回应着她层层包裹的表演。
“雾岛小姐?”
铃木裕也的声音将她从短暂的失神中轻轻拉回。
“是。”
她抬起眼,眸中一瞬的恍惚迅速被温顺的薄雾覆盖。
“你脸色好像……有些苍白?是走累了,还是昨晚没休息好?”
男人微微倾身,关切地看向她的脸。距离控制得恰到好处,不会令人不适,却足够传递温度。
“我们要不要去那边的长椅坐一下?或者……”他顿了顿,语气里多了点不易察觉的紧张,耳根泛起浅浅的红,“我过来时,看见公园南门那边好像有个小型手作集市,挺热闹的,摆了很多有趣的小东西。要不要……一起去看看?就当散散步,转换心情。总是待在咖啡馆和房间里,对心情和身体都不太好。”
他的邀请说得有些磕绊,眼神甚至不自觉地飘忽了一下,完全是那种不擅长主动邀约,尤其面对有好感女性时,会露出的、属于普通人的笨拙真实。
雾岛莲沉默着。
理智的齿轮在颅骨内冰冷高速飞转,进行着缜密的风险收益演算。
她应该拒绝。
礼貌而坚定地拒绝。
每多共处一分钟,被周围潜伏的其他“眼睛”注意、解读,甚至误判的风险便递增一分。
铃木裕也只是个与阴影世界毫无瓜葛的普通人,一个过着平静轨迹的公司职员。
他不该,也不能被拽进她周身越来越浓稠的危险漩涡。
但是……
看着眼前这张与铃木葵眉眼相似、此刻写满毫无伪饰善意的年轻脸庞。
感受着这与她日常所处的、充斥着算计、伪装与死亡气息截然不同的、平和到近乎虚幻的午后。
那具经历了无数次“死亡”与“重启”、早已疲惫不堪的灵魂深处,突然……挣出了一丝微弱得令她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渴望。
渴望这虚假的“日常”能再延长一隙。
渴望能暂时从“雾岛莲”这副沉重枷锁中,偷得一口喘息的空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