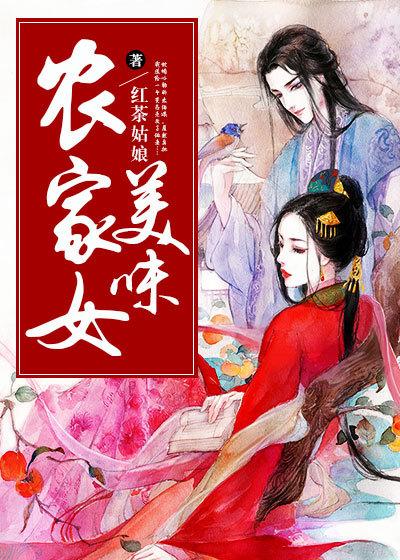九一文学>瑾瑶十三年 > 画金楼(第2页)
画金楼(第2页)
哥哥快从边疆回来了,细下算来他们兄妹二人已经五年没见了。
原本神情淡然的徐瑶此刻也露出笑来。
*
“陵州那边如何了?”
舒砚面色凝重的问。
瑾王府内,舒砚和陆晏知在密室内面对面端坐着。
陆晏知取出一封信递来:“现今陵州正闹春旱,庄稼都快枯光了,流民四起。最近的州府接纳一部分人。不过粮食短缺,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”
舒砚拆开手中的信,一目十行的看完了。指尖轻叩桌面,沉思道:“朝廷不是发了赈灾粮,怎么还如此严重?”
“从离京来看,辗转数次才能达到陵州,一层层瓜分下来,自然所剩无几了……”
“不对。朝廷这次十万的赈灾粮不同以往,转手定不超过三次。若几次下来被扣下些许,最后到手的也不可能才三万有余。”
舒砚手扶着额头,一点点理清思路,盘算这其中有何差池。恍然定睛一处,说道:“信上有个可疑的地方。在陵州春旱之前,这个县尹提前几天在各大铺子预定了粮食,仿佛听到了什么风声似的,而后他又在春旱时施粥济民。”
陆晏知顺着舒砚的思路继续往下道:“确然,但若打好关系,提早得到春旱消息不无可能。你在怀疑什么?为何这人不是为了博个好名声,故意为之?”
“乍然一想并无奇怪之处。但我的人暗自查探到,在这么危难的时刻,数日施粥后,府中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反观府中之人,无一不面色红润,这个县尹还吃得上烤鸡。”舒晏呷了一口茶,继续道。
“如若是博名声还好,可疑的就是,我的人并未在他府上发现余粮。是以,他施粥的粮,从何而来?”
陆晏知良思很久:“府中没有余粮,必定有个粮矿的转移仓,那么可以猜测,他之前的预定粮是个幌子?”
“还不确定,也可能是私下做了什么交易,转移粮矿去了别地或有其他的用处,只是我们没发现……还得亲自去陵州看看。”
话毕,舒砚起身走出密室,“我去同皇叔说一声,明日便出发吧。”
……
翌日一早,天刚蒙蒙亮,晨曦穿透薄薄云层洒落下来。
就在城门刚开锁时,几人悄然离去。
为首的男子身穿件豬色单罗纱衣衫,腰间绑着一根苍紫色虎纹玉带,长若流水的发丝翻动,唯有微蹙的眉头使着平日清澈明亮的桃花眼也透露出几分担忧,这人正是舒砚。
陵州距定京稍远,舒砚此番先去了距陵州较近的上周——那个县尹所在的地方。
他们出行只禀明了圣上,几人暗中行动,蛰伏在外,观察这府中人的一举一动。施粥还是同往日一般进行,不过今日的分量居然比往日还多。
“莫非,他们这是知道我们来访?”陆晏知小声道。
“不会,当时只我与皇叔在场,内侍等都是屏退了,不会走漏风声。应是因为,按他们预定的粮来看,早该所剩无几了,但这个县尹贪了不少,直到现今还有如此多的粮食。他背后之人怕生变故,所以命他赶紧施完粥。”
舒砚端详良久,最后吩咐道:“这里如今查不出线索,留些人守着。我们先去陵州。粮矿快到了。”
前些日的粮食匮乏闹出的动静不小,显然是有人刻意煽动此事。舒砚虽不知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,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安抚流民,稳定民心。
大缙朝国力虽强盛,边关已平定,但开国初期的战事亏损巨大,现今赈灾粮国库确实支撑不了了。所以,舒砚适才所说的粮矿其实是他动用私产买的。
虽然早就入春了,但陵州似是进了夏。
舒砚一行人刚进城门,一阵热气袭来,倒枯燥的热,而是三五成群,四五结对的拥在一起,空气无法流动的闷热。
“诸位不要吵闹,我们是朝廷派来的押送赈灾粮的,这位是瑾王殿下。”
一听是锦王殿下来了,就像在荒漠绝望之际突然撒下了一片甘霖。大家无一不晓,他是年仅十六岁就能领兵上阵,还能打的北狄退无可退。
那时边关战役四起,朝廷军饷供应不起。舒砚直接带兵闯入敌营中抢粮,撑过那段日子,再进行游击,一举歼灭了北狄来兵。
而陵州正是靠近西北,越过塞边的漠川,就到了边境。要是当年没有的瑾王殿下,恐怕陵州众人都得跟着战乱流离失所了。
“诸位多礼了,抗敌和国难本身池玉本责,不必言谢。先吃完饭再说也不迟。”
舒砚示意,施粥棚已搭好了,众人有条不紊的排队领粥。。
舒砚望着天边,担心着另一边的动静。“这也只能撑一时,还须尽快找到被截下的粮矿才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