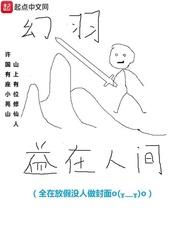九一文学>瞻云 > 6070(第19页)
6070(第19页)
此番过来,就是来看食宿的安排。寝屋一间间看过,膳食录在卷宗上。她在虚室生白台坐下,接了奉上来的竹简一册册阅过。
不知不觉已经夕阳西下,殿中半边借夕照采光,半边点了烛台照明。
她从成堆的竹简中直起身来,挺了挺背脊,揉过酸疼的脖颈,推开窗牖看见倦鸟归林,游鱼入渊,龙首山上金乌最后的光也敛尽了。
“陛下,宫门就要下钥,该回宫了。”庐江在一边提醒她。
她点点头,起身出楼。
楼外马车旁,有人在等她,见她出来急急迎上,“陛下,您要的豆腐脑,还是热的。”
夜幕下,光照不明,她的目光聚在那小小的碗盏上,捧盏的人便有些模糊,莫名地闻声生怒。
不是他。
“快尝尝。”
马车中,齐夏盛了一勺喂给她。
她张口含入嘴里。
“好吃吗?”
天越发地黑了,没有了白日的喧嚣和繁盛,影子在灯下格外狭长。
她盯着那影子,慢慢咽下,“不好吃。”——
作者有话说:来晚啦,发个红包吧
第67章
五月初诏狱令皇榜的张贴,并非去岁新政舞弊的结束,实乃今朝新政的开端。自彭、杨二人牵扯出已故太常温颐,坊间甚嚣尘上。甚至有说法彭、杨二人不仅攀扯了太常,还供出了其他参与舞弊的五经博士。
一时间,太常寺中人心惶惶。
这虽与温冲没有关系,但抱素楼六月的新政就要举行,五经博士们出卷在即,多来心不在焉。他们提不上力,温冲的压力都如山一样抗在背上。
这日回来尚书府见温松,见得温冶也在。
温冶脸色煞白,额渗冷汗,双目涣散,得温冲连唤两声“三哥”方回过神来,勾起了嘴角却扯不出笑,只如砧板上的鱼长喘了一口气。
实乃五经博士中多为温松门生,外头流言纷纷。温冶实在听不下去,方来问温松天子到底何意。
——如此无声无息,任由流言漫天。
当日昆明池上宴,他虽也看出几分蹊跷,但实在想不出动机,又见手足上位,一时不曾不多言。
“这桩事,我本不欲告知你们任何一人。但见你如此义愤填膺,虽是为家族故,但若不知情,来日多受此累。”温松丝毫未理刚到的小儿子,依旧在与温冶说话,“今日知晓缘由,当晓得来日如何自处,如何行事了吧!”
温冶且忧且惊看向父亲。
“当下便有一桩。”温松起身走向温冶,拍了拍他臂膀,“你去教教他。”
话落,离开了书房。
“阿翁!我还有事呢,我……”温冲不明就里,还欲拨转轮椅去追父亲。
“七弟——”温冶拦下他,“你可是为下月新政而来。”
“是啊,我都要急死了。一轮审核算是结束了,这不马上就要二轮删选,然后奉给陛下三审以封卷。但近来我瞧他们心思都不在上头,关键常乐天还时不时过来催促进度,我、我又看不懂……这到底要怎么办吗?”温冲急的恨不得从轮椅上弹起来跑掉。
温冶直待父亲背影消失,方回身推过幼弟,合起门窗安静说话。
“首先,他们心思不在公务上便是怠政,你是他们上峰,该怎么处理便怎么处理。其次,你可知晓他们为何心不在焉吗?”
“不就是近来外头传的那些事吗,八成吓得,心虚了。”温冲摇头道,“我就说做官有甚乐趣,做好是应该,做不好便是这下场。三哥你看看我,可是头发胡子都掉光了……”
温冶懒得同他辩驳,只继续道,“你头发胡子掉落,为的是甚?”
“这还用说?怕陛下罚我!”温冲仰天长叹,“人人都羡慕我一朝得道,做了九卿之首的太常,乃国之栋梁。又道陛下恩重温家,尊师重道,天下效之。实乃君臣和乐之态。其实乐的仅陛下一人,我真真愁死了,恨不得这会就乞骸骨。”
话至此处,他恨声道,“我都乞过一回了,陛下不准,常乐天也不要。”
“你怕陛下罚你,便做好你分内之事,为陛下分忧。譬如当下何人心不在焉,心有戚戚,该上报就上报。至于你不愿做这太常,乞骸骨一次不够——”温冶叹了口气,“我温氏以文传世已有百年,你好歹也稍微读两本书。”
说着,从书柜上择出一本《礼记》丢给他,“翻到《礼器》篇,自己读去。”
温冲接了书,还欲说甚,见兄长已经开门离开,只得低头翻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