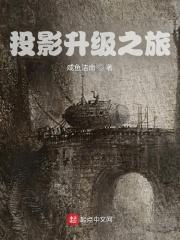九一文学>瞻云 > 8085(第7页)
8085(第7页)
邱枫抬首怯怯,“我们都爱慕州牧大人,打听他的事,说什么的都有。其中有说,他曾与当今天子有婚约,如今又言天子驾临……那晚在您面前,因我和黄姑她们在场,他那样英雄般的人,竟连头都不敢抬,满是窘迫,完全一副讨饶的姿态……婢子、婢子就想到了您。”
“所以你读了那两句诗:云障青琐闼,风吹承露台。”江瞻云笑道,“这首诗表面说对佳人的思慕之意,实乃寓意能者怀志,渴望君王怜才。正好‘青琐闼’、‘承露台’又都是宫中之物,代指宫门。你很聪明。”
“婢子幼时随祖父读过一点书,家中也算诗书人家。奈何战乱水患,天灾人祸,沦落至此。唯剩一兄,在堤坝挑石上工,婢子以浆洗为生。那晚见您,忽生一念,遂尝之。左右若婢子识错也无妨,若是识对了,说不定婢子就有出路了。”
“你想要什么出路?”
“上者得君所顾,赐我读书出仕之明路;中者得见天颜,为臣奴侍奉君侧;下者、下者能见天子,也算平生幸事,就譬如您让我洗衣服,总能多赏赐我一些银钱……”
“有志有勇有谋,朕成全你。”江瞻云颔首,让她将书卷奉来,落上一印,“你执此书与印,去州牧府寻长史薛允,让他安排你读书事宜。新政已经在西五州举行,很快会举国行之,朕在未央宫等你。”
“婢子跪谢天恩。”
“下去吧。”
邱枫又磕一头,捧卷在怀,奔跑出去。
“回来。”闻天子唤住,惶惶回神,却闻她道,“朕今日的衣衫不给洗了吗?”
*
时值薛壑处理完明岁所需的工料回来,却也只是站在门边候了半晌,由着一道少女倩影奔去,目光灼灼对着屋内女郎。
“站着作甚,进来。”江瞻云指了指缸中,“今日我让叶肃挑了整整两缸水,方才邱枫在这,炉子都点好了。”
她一边说一边上来挽他臂膀,手伸一半直接拍了上去,“一身灰,赶紧洗洗。趁现在还有日头,不然到夜里再洗就太冷了。”
“就是,这处夜深霜重,臣奴婢子也不好安置,你一人在此就算能吃苦,我也不忍心。左右再两三日,我就回州牧府了,你要不今个就先回去吧。”薛壑从片刻前对江瞻云满目的敬佩之情中回过神来,被拖着也不肯往里走,只一个劲劝她回去。
她从齐国郡跑来金堤上,对他许下诺言。
他很开心。
她说要留在这处伴他过两日寻常百姓的日子。
他很感动。
但真的够了。
没有一刻,薛壑比现在企盼,她快些离开他。
——她根本就是来报复他的。
譬如这会,她拴门合窗,眼看就要剥光他的衣服。若真动手反抗,她自然不是他对手。
但他怎么真动手?
便只好由着她脱,由着她挽袖给他擦洗,由着她又摸又搓又哄。
“你、好了吗?”薛壑靠在木桶沿上。
“好了,差不多了。”江瞻云温柔又贤德,扑闪着一双雾蒙蒙的眼睛,拧干巾帕给他。
“当真?”薛壑睁开眼,忍过小腹早就酿起的阵阵热潮,赶紧接来帕子出浴。
江瞻云把衣裳捧来,掀帘去了里间,说要歇晌。
薛壑套了一件中衣入内,掀开被褥抱她,却不想被她拍开了手。
“不是说好了吗?”
“对啊,我说你沐浴差不多了。”
薛壑坐起身来,“那你还没好?”
“昨日擦药你没看吗?”江瞻云从案头拿了一个小药盒给他,“左右上榻了,那再涂一会,早涂早好。”
她说她走得急,所以没带衣衫,没带钗环,没带奴仆,甚至连护身禁军都是翌日才传来的,但她偏偏没忘记带这么一盒药。
让他涂。
让他日日看着,摸着,反省着当时的蛮干和事后的逃跑。
即便十五年前,他就知道他未来的妻子是个睚眦必报的人,但着实没有想到,能睚眦必报到如此地步。
他生无可恋地接了药盒,卷起她里裙,“我瞧着好了,不肿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