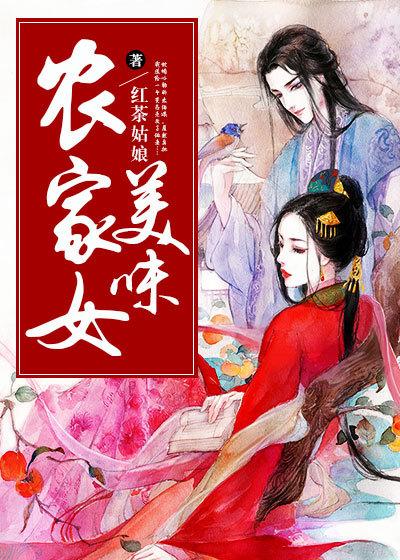九一文学>骆萧山的美食日志 > 画中筵席(第1页)
画中筵席(第1页)
骆萧山连忙摆手,她是不介意啦,这种事情,不应该取决于主人介不介意吗,她可没有给缪与添麻烦的意愿。
这位可是隔空接触了一下愚蠢人类(指山下的小孙),都要洗手洗半天的大爷,外套她还能洗了再还给人家,总不能把缪与的四件套也一并带回山下吧?
于是就站在原地,克制着左右打量的幅度,思考缪与先前说的“显示器”在哪。
她的理解,这能做显示器的东西,也应该是个镜子之类,能反光的平面,可屋里几乎没别的陈设,总不能,总不能是这半杯水吧?
骆萧山的目光掉进床头的半杯水里,想象中自己和缪与轮流眯着眼睛看水面的场景,着实有点好笑。
“渴了?我去给你找——”
“不用不用,一点也不渴,先干正事吧,不然天都黑了,我还要下山呢。”
“寺里也有给女性施主的禅房,不用急着下去。”
他虽这样说,手中的动作没停下,从柜子里翻出一根一指长的白蜡烛,插在一个看上去就有点年头的莲花造型烛台上,递给骆萧山。
后者接在手里,觉得这东西重量有点不对劲,轻飘飘的,跟纸叠的一样。
“确实是纸做的。”
没做额外的解释,缪与打了个响指,蜡烛顶端应声跳出一团光亮,不是火光常见的橙红色,也不是缪与法术的那种青色,而是一抹有点儿超现实主义的粉红色。
还是那种浓度很高的,几乎和现实世界不在一个图层的艳粉色。
骆萧山的吐槽脱口而出:“这好像情趣酒店的灯……”
缪与重重咳嗽一声,白她一眼,没好气地说:“你又知道了?”
“没吃过猪肉,还能没见过猪跑吗?”
说归说,骆萧山也就是嘀咕一句,缪与叫她端着烛台站在墙边,她就乖巧老实地立在那里,一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的盯着烛火,好似里头会跑出来什么了不得的小妖精。
还是缪与叹了口气。
他将什么东西装进口袋衣兜中,向她走近,伸手挡了一下她的眼睛:“不要盯着看,有致幻效果。”
“致幻?类似于吃了毒菌子?”
别说,网上这样的帖子可多,什么大象公交车,青蛙护士的,要不是听说对肝肾大脑都是不可逆的负面影响,在最年轻无畏傻大胆的时候,她也不是没有好奇过。
哎,珍爱生命,远离躺板板的红伞伞。骆萧山昨天还拿着村里的大喇叭到处宣传来着。
缪与却说:“不是一回事。这种焰火能够唤起人心底的欲望,但欲望不一定是好东西,一不小心,就没法再回头。”
“你这话说的好像个谜语人。”骆萧山没听懂。
眼前的人表情严肃,额前的碎发盖下来,几乎遮住眼睛。他朝骆萧山伸出手,掌心向上,示意她牵住自己,拿起矮桌上的半杯水。
“哗啦!”
手腕一转,竟将那杯水尽数泼向了身侧的墙壁。
骆萧山下意识想躲飞溅的水,差点没反应过来。
之前仔细打量这屋子时,并没有对墙体多加注意,不过是土砖砌成的,抹了层灰浆,呈现出一种陈旧的土黄色,表面呈现粗糙不平的颗粒状,是乡村老屋里最常见的样子。
可此刻,被水泼湿而颜色加深的那块,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。
墙皮仿佛活了过来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四周无声地褪去,形同退潮。而底层被掩盖的东西,正在显露真容。
是一幅画。
最先被看到的,是一只由水墨线条勾勒出来的酒爵,斜上方一道栩栩如生的水流正凌空注入其中。
骆萧山并不想眨眼,但手上蜡烛的火光实在炫目,她无法确定,那道水流是否是真的如同她所见那样,真的在潺潺流动。
一幅……会动的画?
骆萧山不知这是否就是缪与口中的致幻效果,但是不是哪里出了点问题,怎么,她心底的欲望,其实就是想在墙上看电视?
她是卖投影仪的吗?
无论心中作何想,墙皮褪去的范围越来越大,其下的画卷面向屋中人逐渐现出全貌。
正倾倒酒液的杯爵属于一场盛大的古人夜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