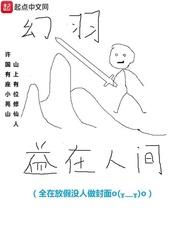九一文学>带着夫郎打天下 > 2230(第13页)
2230(第13页)
陈焕拍了拍他的肩,安慰道:“能活下来,比什么都强。”
两个流民苦笑着,随即哀戚地点了点头。的确,对他们这些人来说,活着,就好。
沉默片刻,陈焕忽然问道:“我听说……占了南阳的那伙人,领头的是个很凶悍的角色?”
年长的流民听到问话,脸上露出一种近乎麻木的茫然,他扯了扯嘴角,“凶悍?”
他顿了顿,勉强算是在笑着,“这年头,手里拿着刀枪、能拉得起队伍的,哪个不是凶神恶煞的样子?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,官军来了抢,乱军来了也抢,土匪来了更要抢……一样的,都一样,没什么分别。”
一旁年轻的流民却对那伙义军印象深刻,他认命了,可又不甘认命。那些义军口中的话,他记得清清楚楚!
“孟儒。”他忽然道。
年长的流民闻言,怔了怔,随即低声呵斥道:“你胡说什么!不要命了!”
这些人不过是送了他们两件破衣裳,一点干粮,就当他们是好人了?什么话都敢说,万一……怎么死的都不知道!
可年轻的流民不服,他双手撑着地,似是回忆起那惨痛的经历,他双目血红,怒吼一声:“他叫孟儒!”
他永远不会忘记。
见状,陈焕眼中掠过一闪而过的惊惧,旋即一脸愤概地拍了拍那人的肩,“唉……果真如此!”
他摇了摇头,微叹了一声,仿佛不忍再听。随即他站起身,掸了掸衣袍下摆,“夜深了,二位老乡也早些歇息吧。”
那年轻的流民忽而攥住他的衣摆。
陈焕心生了一丝胆怯,却又不得不装作镇定,他回过头来,僵硬地笑着,“怎么了?”
“……你的酒囊没拿。”
陈焕这才接过酒囊,快步离开了此处。
待陈焕离开后,角落里靠着树干闭目“睡着”的人忽然醒了过来。
次日,行军休息之时,便有一人将这件事禀报给了景谡。
之前在吴县时,景谡便听闻,陈焕此人对天下大事、各方势力了如指掌。
但在景谡看来,陈焕像一颗被刻意投入棋局的棋子,看似无害,却随时可能搅动整个局面。
正在他思忖之际,前方忽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。
来人正是景家军的信使,焦急地下马,信使单膝跪地,双手呈上一封密报,气息都尚未喘匀,“公子,将军急报!”
景谡接过密报,粗略看了一眼。
原是景巡所领的主力军,本来都快到南郡秋泽县了,不料行军途中,意外惊扰了盘踞于山林深处的一处寨子。
此寨约百余人,是此地的流寇,极其擅长利用地形设伏,弓弩陷阱刁钻狠辣。
先锋斥候遭遇伏击,折损了十余人后,景巡将军已下令,务必剿伏此寨。
景谡眸色微深,秋泽县、黑虎寨。
他记得这个地方,只不过时间稍微提前了些。
前世,是在景家军已占据秋泽县,安抚地方时,才从当地百姓涕泪交加的控诉中,听闻了这黑虎寨的种种恶行。
劫掠商旅、绑票勒索、甚至时常下山骚扰村落,强抢粮食物资、绝人生路,可谓是恶贯满盈。当时是为了安抚民心、肃清后方,景巡才派兵剿抚。
而如今,却是在行军途中便正面撞上了。
黑虎寨位于秋泽县西南三十里处的“黑虎山”,山势险峻,林木葱茏,易守难攻。
寨主彭黑虎,原名不详,并非寻常莽夫,据说早年曾在边军待过,因犯事逃亡至此,拉拢了一批亡命之徒和活不下去的流民,凭借其懂些粗浅兵法和对地形的利用,渐渐成了气候。
寨中约有一百五十人左右,核心是二三十个跟着彭黑虎多年的悍匪,其余多是依附的流民。
他们确实极其擅长设置陷阱,利用山石、竹木、藤蔓制造绊索、陷坑、滚木礌石,甚至擅长胡人常用的弩箭,在箭上淬了山林间的毒草,虽不会立即致命,但中者伤口瘙痒,引得人不停地去抓挠,直至伤口溃烂而死。
若正面强攻,即便攻下黑虎寨,但对他们这支不足千人的军队来说,必定损伤不少。
思及此,景谡心中已有决断,他极快地书写了一封密信,让信使以最快的速度传回叔父手中。
待信使离开,原来禀报陈焕之事的亲卫开口问道:“公子,陈参事那里……”
陈焕……